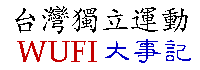訪問:
許維德、林朝億、張信堂、陳育青、黃淑惠、陳妙姗、林秀珊
時間:2007年4月13日晚上
地點:台北市杭州南路
台獨聯盟辦公室

前言
在海外台獨運動的發展史中,1970年絕對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年。
就在這一年的1月1日,海外台獨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團體──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今「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前身) ,於美國的紐約市宣告成立。也是在同一年的1月3日,從1965年開始就被國民黨當局軟禁的彭明敏,順利搭乘飛機逃離台灣,並於隔天抵達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尋求政治庇護。然後,三個多月後的4月24日,具台獨聯盟盟員身份的黃文雄和鄭自才兩人,在紐約市試圖開槍刺殺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的台灣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雖然他們的行動失敗了,但卻在第二天登上了國際各主要媒體的重要版面,為台灣人尋求獨立自主的訴求在國際社會做了一次重要的宣傳。
這驚天動地的一槍,已經是發生在三十七年前的事件了。不過,我們卻覺得,這一槍的確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正是在這樣的考慮下,《共和國》雜誌決定在「刺蔣案」三十七周年的這一天推出〈四二四刺蔣專輯〉,並順利連絡到該案的主角之一──鄭自才先生,對他做了將近三個小時的專訪。
關於這個訪談錄,擔任文字撰寫工作的筆者有幾點說明。
首先是鄭先生的名字。鄭先生的原名是「鄭自財」,這也是他在所有和「刺蔣案」相關之文獻中出現的名字,雖然部分媒體在他剛返台的1991年也曾經以「鄭自才」這個名字稱呼他。不過,根據相關媒體的報導,他已經在2004年將其登記的名字改為「鄭自才」。在這種情況下,既然我們是在2007年的四月進行這個訪問,而訪問時其主角的名稱為「鄭自才」,因此,我們原則上將沿用「鄭自才」這個「當下」的名稱來稱呼鄭先生。
第二是關於書寫體例的說明。筆者在訪談錄中決定同時交叉使用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最基本的原因在於,雖然這個訪談錄基本上是依據鄭先生的現場訪談資料寫出來的,不過,我也還參酌了一些現有的相關文獻資料,因此,如果這個訪談錄全部採行第一人稱之敘述方式的話,筆者會覺得有些愧對鄭先生,因為我並不是完完全全依據訪談資料「如實地」將訪談內容整理出來的。在這種考慮下,我刻意加上第三人稱的敘述方式。在這個部份,一方面我可以對原始訪談資料作進一步的剪裁,幫助讀者的閱讀,另一方面我也可以適度加上訪談以外的文獻資料,而不會被讀者誤會成是訪談過程中鄭先生自己所講的內容。
最後是第一人稱部分的書寫文字說明。由於這個訪問基本上是以鶴佬話進行的,在整理訪談逐字稿的過程中,筆者也是盡量依照鶴佬話的發音方式,將整個對話過程轉為文字稿。

出國前的歲月
鄭自才於1936年出生於台南市,父親從事水果批發的小生意,母親則是家庭主婦。鄭在家中排行第三,上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下有四個弟弟。
鄭在1942年進入台南市「台南寶公國民學校」(今「立人國小」)就讀,在1945年國民黨接收台灣以前,總共於日治時期讀了三年的日本書。由於躲空襲之頻率太高的原因,鄭表示,雖然讀了三年的日本書,日文卻幾乎都忘光了。
雖然如此,在訪談當中鄭依舊表示,他對這三年的「日本教育」還是有一些印象:
「你入去教室,就ài褪鞋仔。教室頭前攏khǹg足濟[鞋],你ài褪赤腳[打赤腳]入去內底[裡面]。擱老師真歹án-ne,gia̍h一枝chhôe-á[棍子]外長--ê,會凍[可以] sut到[打到]後壁[後面] ê人án-ne。」
此外,戰爭末期的空襲,鄭當時年紀雖然還小,但也還有印象。
「空襲ê時陣擱有印象。空襲ê時陣看彼lō[那個]火燒,古早厝攏一層niâ嘛,看火燒,壁mā倒去,磚仔壁倒去啦,ah火燒啊,ta̍k-ê[大家]攏kōaⁿ[拿]包袱仔走啦,這是擱有印象啦。」
1945年,國民黨軍隊接收台灣,鄭在學校中所接受的教育內容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從原本的日文教育轉變成國民黨體制的漢文教育。不過,由於戰後初期能以北京話教書的老師還十分有限,在鄭進入國民黨教育體制的前幾年,老師甚至都是以鶴佬話當作教學語言的。
鄭在小學的成績算是中等,因此,學校畢業以後,老師就建議其去報考職業學校。雖然鄭的雙親對於他該讀什麼科系並沒有什麼概念,不過,當時有一位同學的父親,認為讀「建築」以後比較容易賺錢謀生,所以鄭就在小學畢業的1949年懵懵懂懂地考進了「台灣省立工學院附設工業職業學校」(今「成大附工」)建築科就讀,也沒有再考慮去考其他的普通中學,而且在該校一讀就是六年。在這所學校,由於所有的學生都是台灣人,完全沒有外省小孩,所以多數老師講課都是用鶴佬語進行的。當然,該校還是有一些從中國來的老師。不過,對當時的鄭而言,他似乎並沒有辦法去區辨這些老師和台灣人老師在政治立場上的可能歧異。他這樣表示:
「知影中國來ê老師kap台灣ê老師無啥kâng[不太一樣],但是,彼陣仔擱分bē清楚,台灣來ê老師kap中國來ê老師,tōa[在]政治上有啥物區別。彼陣仔擱無leh。」
1955年,鄭從「附工」畢業,並在一番苦讀以後,成為班上考取大學的兩名學生之一,考進了「成功大學」的建築系。鄭在學校裡還是把多數精力都投注在專業領域上,一方面專注於學校課業上,另一方面也擔任系上刊物《百葉窗》的主編。現任「世界宗教博物館」館長的漢寶德,在當時不但是鄭的同系同屆同學,同時也常在《百葉窗》上發表文章。
由於鄭在學校的表現相當不錯,大四的時候,有一個在系上教水彩的中國老師就邀請他加入國民黨,不但拿入黨的申請表格給他,要鄭填完後再交還給他,並且還對鄭說明入黨的種種好處。當時的鄭似乎頗有年輕人的正義感,他這樣敘述他對這件事情的反應:「我就想講,ah入黨有chiah[這麼]濟好處,無入黨就無,這無公平--a,就kā拒絕--a,我就無加入--a。」因此,鄭並沒有因為這位老師的邀請而加入國民黨。沒想到,這個決定卻真的影響了他後來在系上擔任助教的機會(詳見後述)。
1959年,鄭大學畢業,以預備軍官第八期的身分入伍服役,抽到海軍陸戰隊,駐地在高雄左營。入伍的經驗,對鄭這個一直都窩在校園內之象牙塔的知識份子而言,確實是有一些影響和衝擊。他這樣表示:
「做兵ê時陣,感覺無啥著,這寡大學生,h³老芋仔欺負,有這lō感覺啦。…… 一個受khah[比較]高教育--ê,h³無受教育--ê訓練、欺負,有這lō感覺啦。」
然而,這種不公平的感覺,似乎並沒有從根本上挑戰鄭在學校中所被培育出來的政治信仰。反倒是退伍後的求職經驗,對他的政治之旅反而有更深刻的影響。由於鄭在學校的表現不錯,他在入伍前就已經通過系主任的面試,要他在退伍後到系上擔任助教。1960年退伍後,鄭就回母系展開他的職場生涯。然而,在他工作了兩個禮拜以後,學校又突然收到通知,說該系不能聘任他當助教,原因是他不具備國民黨黨員的身分。這個經驗讓他對這個所謂的「黨國體制」,頓時萌生了相當程度的不解和不滿:
「這個代誌[事情],h³我對成大有一寡意見啊。這個大學,結果受著黨ê控制,你beh tī[要在]大學敎冊,你一定愛入黨啊。這就是真無公平ê所在嘛。一個黨,結果有法度去影響一個大學ê教授、職員。」
既然無法在系上擔任助教,鄭就先上台北補習,準備出國讀書的事宜。後來,設立不久的「中原理工學院」新成立建築系,鄭就到該系擔任助教,一直到1962年到美國留學為止。
談到為什麼要出國讀書,鄭這樣表示:
「彼個[那個]時代hⁿh我講ê 60年代,會使講[可以說]是一個苦悶ê年代。所有ê大學生,攏想beh[要]出國,beh離開台灣就著啊,愛想辦法離開。我teh做兵ê時陣,mā chiâⁿ[很]濟朋友,攏leh講愛申請學校啦,teh互相討論講愛án-chóaⁿ申請啦,ah批[信]愛án-chóaⁿ寫,攏有leh討論chiah-ê代誌。Ah請學校,我是對做兵ê時陣就開始請啊。Ah彼陣ê氣氛,就是講我愛離開,愛離開台灣。Ah彼陣就是ta̍k-ê[大家] chiâⁿ[真]鬱卒--ê hⁿh,ah想beh脫離這個環境。」
鄭後來申請到美國三間學校的入學許可,包括位於匹茲堡(Pittsburgh)的「卡內基理工學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今「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建築研究所。該校同時給予鄭全額的獎學金,他因此決定到這所學校就讀。在拿了母親的首飾去典當,並向學長借了三百元美金而籌措到旅費後,鄭於1962年的八月正式揮別了台灣,坐著包機飛向了新大陸,展開人生的另一個階段。
在美國加入「台灣獨立聯盟」
鄭在到匹茲堡讀書以後,也不知道台獨團體是透過什麼的管道而收集到他的通信地址,他收到了日本台獨運動團體所發行的《台灣青年》雜誌,並逐漸對這個雜誌所提出的台獨主張開始感到認同。
此外,他也碰到了一些具有台灣意識的留學生,比如說有個讀物理的留學生,叫做王俊明,就對鄭的政治意識啟蒙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在當時,多數的留學生都還延續在台灣的習慣,使用北京話當作彼此之間的主要溝通語言,但是王卻對這個現象提出了質疑:
「彼當陣[那時候],可能受著國民黨教育ê影響,tī留學生ê circle內底,攏講北京話啊。王俊明就kā我講,ah你是beh[要]講北京話chhòng啥[做什麼]?H³我一個shock[衝擊]啦,我tī hia[在那裡]開始想講,eh,北京話kap台灣話無kâng喔。」
當然,活在當時民權運動日益高漲的美國社會裡面,這個時代氛圍也對鄭之反抗意識的模塑有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在美國求學的第二年,鄭從匹茲堡坐車到華盛頓特區,特地去參加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金恩博士在那裡所組織的示威活動。他這樣說明自己會關心這些活動的動機:
「我到美國,就開始注意chia散赤人[窮人] kap好額人[富人] ê無kâng啊。看一寡美國ê冊hⁿh,ah彼本《Poverty in America》,《散赤tī美國》,我有看,ah就開始對這個弱勢、受欺負--ê表示同情啊。Ah彼當時白人欺負烏人……。」
在這種氣氛下,鄭於1963年赴美求學的第二年,就加入了「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今「台灣獨立建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前身),正式成為台獨運動的一份子。
此外,也是在匹茲堡,鄭認識了他的前妻黃晴美,並在1964年與黃結婚。黃也是在1962年從台灣到匹茲堡留學的,不過,她讀的並不是鄭所就讀的「卡內基理工學院」,而是「匹茲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也是在鄭與黃結婚的1964年,黃晴美的哥哥黃文雄申請到了匹茲堡大學的獎學金,開始就讀於該校的社會學研究所。不過,在黃文雄到匹茲堡讀書的時候,鄭已經從學校畢業,並開始在馬利蘭州巴爾的摩(Baltimore)的建築師事務所工作了。
1965年,鄭的大女兒出生,同時他也在位於紐約市、相當著名的「Marcel Brueuer建築師事務所」找到新工作,全家搬到紐約市附近的紐澤西州居住。鄭一方面忙於專業生涯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十分熱心於台獨運動的推動,不但被選為改組後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的中央委員,同時也憑藉其在美術設計上的專業能力,為《Independent Formosa》這本台獨聯盟出版的英文雙月刊設計雜誌封面。
1967年,鄭的兒子出生。
刺蔣的計畫和準備
1969年9月,全球性台灣獨立聯盟籌備會議在美國的紐約召開,來自美國、加拿大、歐洲和日本的各地台獨組織同意成立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當時鄭也有參與該次會議。1970年1月1日,該組織正式對外宣佈成立,由蔡同榮和張燦鍙分別擔任該組織的正、副主席。也是在1970年,當時擔任台灣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應美國國務卿的邀請,計畫赴美進行十天的訪問。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鄭等人萌生了刺殺蔣經國的想法。
談到當初為什麼會有這個刺蔣的計畫,鄭直接表示,這幾乎是當時很多海外台灣人一致的想法:
「彼當時ê留學生,會使講[可以說]所有ê攏有這個想法。就是講政權beh án-chóaⁿ ián[推]會倒,ián bē倒ê時,你可能愛用一寡極端ê步啊,就是暗殺ê步啊。Ah暗殺這個物件,tī島內真困難啊,ah彼當陣有一個消息講,蔣經國beh訪問美國啊,ah彼當陣就真濟人有這種想法啊。Ah愛án-chóaⁿ去刺殺蔣經國啦。」
當然,會萌生這樣的想法,和當時波瀾壯闊的六零年代時代背景,應該是脫離不了關係的。鄭這樣表示:
「Ah tī美國彼個年代,就是越南戰爭ê年代嘛,ah學生運動ê年代。所以足濟[很多]學生運動反對越南戰爭。Ah阮彼陣mā反越戰,góan彼陣會使講是相當ê radical[激進]。頭毛[頭髮]攏留足長--ê。」
「當然我彼陣決定beh做這個代誌,時空ê背景,影響足大--ê,親像講越南戰爭ê影響,he越南人hⁿh,為著in[他們]國家ê統一,獨立,in mā犧牲khah大hⁿh。擱[還有]彼個[那個],Palestine[巴勒斯坦] kap[和] Israel[以色列] ê對抗,彼當陣ê報紙,ta̍k日[每天]都有死傷,ta̍k日都有彼款[那樣] ê代誌發生嘛。擱彼lō北愛爾蘭,North Ireland,beh脫離英國,喔,彼個戰爭mā真激烈--ê啊。Ah h³我ê影響kap感受就是講,ah人為著ka-tī ê國家ê獨立,人犧牲性命hⁿh,比咱[我們] án-ne幾若[好幾]百倍--ê,ah咱這犧牲算啥?所以彼陣就是講,這應該來做。Ah m̄管是犧牲後果án-chóaⁿ,就是咱愛來做--ê,彼陣ká-ná[好像] án-ne[這樣]想niâ。」
至於到底是誰首先萌生了「刺蔣」的具體想法,鄭表示他是這個計畫的原始構想者。由於黃文雄是鄭的姻親,而且當時也正住在鄭的公寓中,所以黃是鄭這個計畫的第一位加入者。此外,鄭也還找了當時擔任「台獨聯盟」組織部負責人的賴文雄參與該項計畫,再加上鄭的妻子黃晴美也一直都很清楚鄭的打算和想法,所以,這個計畫的參與者總共有四個人:鄭自才、黃文雄、賴文雄和黃晴美。根據鄭自己的話語,這個刺殺計畫的參與者包括:
「我啦,ah黃文雄,黃文雄hⁿh,因為伊tī[在] Pittsburgh[匹茲堡]了[以後],就申請去Cornell[康乃爾大學]。Ah Cornell離New York真[很]近嘛,ah伊有時間,若放假--a,iah是有時間,就走來New York chhōe阮嘛,ah就tòa tī我hia[那邊]嘛。所以這項代誌,我就有kap伊講,有招伊啦,所以伊有加入啦。」
「了[之後]我有擱[再]去chhōe賴文雄,講這個代誌,你mā愛來參與,án-ne。」
「Ah有參與--ê,當然黃晴美有參與,伊知影[知道]這個代誌。」
其中,黃晴美的角色十分特別。她不但同時是鄭自才的妻子與黃文雄的妹妹,同時也是這四個人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有訪談者問鄭說黃晴美到底知不知道他的這個計畫,鄭是這樣回答的:
「伊知影[知道] hⁿh,伊不但無反對,擱支持啦。我感覺這是台灣女性偉大ê所在啦,tī彼個所在,彼個時陣,因為這項代誌,做落去ê時陣,我若m̄是去hông關,就是去hong打死ê時陣,這個家庭伊愛擔(taⁿ) án-ne。Ah彼當陣我認為講,晴美是有這個能力hⁿh,將這二個gín-á飼大啦,因為第一伊是讀英文系--ê嘛,所以英語能力好嘛,tī美國beh chhōe頭路,應該無問題啦,所以chiah[才]會決定講hⁿh,來做這個代誌。」
在有了「刺蔣」這個想法並找上了黃文雄和賴文雄以後,由於鄭當時擔任「台獨聯盟」總本部的祕書長,知道當時在路易斯安納州、負責聯盟島內工作的陳榮成手上有槍枝,於是鄭就和陳連絡,要他帶兩把手槍來鄭在紐約皇后區的住所。根據鄭自己的話語,這件事的過程是這樣的:
「因為我彼陣tú好[剛好]是世界聯盟ê秘書長嘛,hⁿh,我知影[知道]陳榮成tī Louisiana有買一寡槍,有leh練槍有啥嘛hⁿh,因為對島內ê khang-khòe是陳榮成teh負責--ê,hⁿh。」
「我ùi[從] New York khà[打]電話h³伊,講你準備兩支槍hⁿh,kap槍子[子彈],你the̍h來h³我án-ne。Tī事前伊就飛飛飛,飛來tòa tī我Queens[紐約市皇后區] ê apartment[公寓]。」
那麼,陳榮成到底知不知道這個「刺蔣」之計畫的存在呢?他又到底算不算是這個計畫的第五個參與者呢?對於第一個問題,鄭的回答是肯定的;至於第二個問題,鄭的回答則是否定的。當其中一個訪談者問鄭,陳榮成在送槍到紐約市的時候到底知不知道這些槍的可能用途時,鄭是這樣回答的:
「Ah伊來我有kā[跟]伊[他]講啊,講這是啥物用途--ê。Ah伊物件the̍h h³我,ah彼陣tú好[剛好]暗時[晚上]啦,ah伊the̍h h³我了[以後],就離開啊。Ah我相信伊離開了後[之後],一定是去蔡同榮hia,去報告啊,kā主席報告啊,報告講伊the̍h啥物物件,足重要ê物件,hⁿh。」
在這個意義上,雖然陳知道「刺蔣」計畫的存在,然而,由於他並未直接參與該計畫,所以似乎不能真的算是該計畫的執行者和參與者。
鄭在從陳榮成手中拿到這兩把手槍之後,也曾經找這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到紐約長島(Long Island)進行射擊練習。鄭在訪談中這樣描述這次的練習過程:
「The̍h著這個槍了[之後],阮有去練習啦。The̍h這個槍,駛我彼台Volkswagen,因為New York無所在啊,所以駛到Upsstate New York[紐約上州]去hⁿh,tī leh山頂chhōe無嘛,chhōe無會凍[可以]練ê所在,ah經過一間賣槍--ê,賣槍--ê我入去買beh練ê槍子[子彈],結果彼個[那個]有紀錄啦,因為伊槍仔beh賣,伊就愛登記啊。所以有登記。」
紐約上州的山上找不到適合的射擊練習地點,他們就改到紐約的長島海邊,找尋其他的可能練習地點。
「Long Island[長島] tú好[剛好]海邊嘛,ah彼工m̄知án-chóaⁿ,Long Island攏無啥物人,ah海風sngh-sngh[呼呼]叫。入去海邊,ah沙灘邊仔,攏一欉一欉細欉樹仔[樹木],ah低低啊,ah人nǹg[鑽]入去樹仔內底,ah練啊,the̍h彼個Coca Cola [可口可樂] ê矸仔[瓶子],ah練he槍啦。」
1970年4月18日,蔣經國終於抵美進行訪問,首站是洛杉磯。台獨聯盟散佈於全美各地的盟員,也隨即在蔣經國所到之處舉行多場示威遊行。首先開場的,正是洛杉磯的示威。4月20日,蔣飛抵華盛頓郊外的安德魯軍用機場,60位台獨聯盟盟員即手持「我們代表沈默的台灣人」及「台灣人要自決與自由」等標語在機場外抗議,並高喊口號。當天示威的指揮者就正是鄭自才。
在組織了華盛頓的這場示威以後,台獨聯盟的幹部又立刻在紐約市召開會議,準備在蔣來到紐約市的4月24日那天也舉行另一場抗議活動。鄭心裡決定,在蔣抵達紐約市的時候,也就是他們這個刺蔣之計畫付諸實行的時候。由於鄭打算在當天實施刺蔣的計畫,他也就不再適合擔任該次示威活動的指揮。在鄭推辭掉這個示威總指揮的工作以後,其他盟員只好另推剛入盟不久的Chester Hsieh擔任這次任務的指揮工作。
4月23日,鄭等人在鄭宅召開了刺蔣計畫的最後一次行前會議,討論一些更細節和技術層面的問題,包括如何將槍帶到現場、由誰開槍、怎麼開槍、現場的任務分配等。他們的決定是由黃晴美把槍放在她的皮包裡面,等到現場以後再交給計劃要開槍的黃文雄。至於開槍的那個人,黃文雄則自願由他來擔任,理由是這幾個同志中只有他還沒有結婚,比較沒有家累。鄭這樣描述這個開會的過程:
「當然是講siáng[誰] beh開[槍] ê時,大家攏無意見啦,tiām-tiām[靜靜],tiām-tiām啊。最後我無法度啊,我講我開嘛,我講án-ne了後,黃文雄講bē使[不行],bē使,你有某[妻]有kiáⁿ啊,這犧牲太大啦。伊講伊beh開啦,伊講伊猶未結婚--ê。伊就決定伊beh開。」
就這樣,一切大抵準備妥當,刺蔣計畫已經箭在弦上了。

四二四刺蔣案
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從華盛頓抵紐約市拉瓜地亞機場,隨即乘車進入市區,前往坐落於第五大道的廣場飯店(Plaza Hotel),計劃於中午時分抵達飯店,對「遠東美國工商協進會」的會員進行演講。在該場演講開始以前,飯店對面就已經聚集了30多位台灣人,對國民黨在台灣遂行的獨裁統治進行示威抗議活動。
至於打算刺蔣這邊的人馬,根據鄭的記憶,他們(鄭自才、黃文雄以及黃晴美)三個人在4月24日當天,係由蔡同榮開車將他們從皇后區載到曼哈頓去的(黃文雄則對這件事有不一樣的記憶)。根據前一天會議的任務分配,黃文雄將開槍射擊蔣經國,而鄭的工作,則是在人群中散發該次示威活動的宣傳單,順便觀察敵情。而賴文雄,則並沒有分配到什麼特別的任務。鄭這樣回憶事件正式發生前,他們之行動佈署的梗概:
「Tī[飯店前面的]噴水池邊仔se̍h[繞],tī[在] hia[那裡]遊行。黃文雄是講伊先入去看整個ê情形啦,hⁿh,ah我任務是hⁿh,the̍h he[那個]遊行ê傳單嘛,hⁿh,tī leh頭前[前面]分,ah我tú好[剛好] tī hotel ê頭前。」
蔣經國於12點左右乘坐轎車抵達該飯店,並在警察的護衛下登上石階,走向飯店門口。鄭這樣描述整個槍擊的過程:
「Ah我leh分傳單ê時,就有看著蔣經國啊,坐tī[車的]後座。到門口ê時陣,人kā伊開門,伊就行入去Hotel Plaza[sic, Plaza Hotel]。Hotel Plaza ê樓梯,有差不多兩個所在,愛爬(peh)差不多三gám嘛。頭一擺三gám,ah一個平台,擱差不多三gám,án-ne hⁿh。」
Ah[整個飯店門口]攏是情治人員啦,New York City e uniform[制服]警察,便衣--ê,ah擱state[州的]--ê,ah擱聯邦政府--ê,擱伊[蔣經國] ka-tī chah[帶]過去ê保鑣--ê,喔,足濟人攏圍tī hia。Ah伊足濟人ê時,伊mā m̄知你是m̄是情治人員啊,所以黃文雄藏(chhàng) tī內底,in[他們] mā m̄知伊是啥人啊。」
「Ah蔣經國就行入去啊,行入去,ah伊中ng[中間]彼個門是旋轉門,所以行beh到旋轉門ê時,ah文雄就開槍啊。」
「Ah開槍ê時,伊邊仔攏khiā警察仔,ah手giâ起來,in[他們]警察攏有訓練嘛,ah in看伊手giâ起來,就kā lóng[撞]落去。[槍]開落去,伊直kā lòng落去,lòng落去就差差不多20 centimeter,就開tī伊頭殼頂。」
「第一槍打落了後,“póng”一下足[很]大聲,就亂啊嘛,hⁿh,ah警察就kā[將]黃文雄手sa[抓] leh,就jí[按] leh塗腳[地上]啊嘛,伊就無機會開第二槍啊嘛。」
在黃文雄開槍以後,原本在外圍分發傳單的鄭,一看到黃文雄被壓制在地上,就立刻衝上前去,本能地想要支援黃文雄,但卻也立刻被現場的警察擊倒在地,頭部當場流血受傷。鄭是這樣回憶這段過程的:
「[黃開了槍以後,] ah有ê人就走啊leh,走--ê走,ah我彼陣就leh分宣傳單嘛,看黃文雄hông jí[按] leh塗腳[地上] h hⁿh,我就走過去,我若無過去我可能mā無代誌,我衝óa[接近]去,衝óa去ê時陣,h³警察用棍仔kā我mau[打]一下hⁿh,mau到我ê眼鏡,我頭殼chia就thīⁿ[縫]五、六針嘛。Lòng一下流血leh,就m̄知人嘛。到尾仔黃文雄h³警察jí[按]落去,伊就tòa hia[在那裡] hoah[喊]嘛,let me stand like a man[讓我像個男子漢一樣地站起來] án-ne,叫警察h³[讓他]爬(peh)起來án-ne。」
之後,黃文雄和鄭都分別被捕,並立刻被送往警察局。鄭表示:
「Ah警察就kā阮二個,手銬反銬án-ne,就kā阮送入去警察車啊嘛,ah警察車就駛入去警察局嘛,所以彼一工,就kan-taⁿ[只有]阮二個hông掠去。」
因為鄭的頭部流血,所以又立刻被警察送到醫院去。在醫院的時候,鄭在其所穿著的雨衣中摸到一顆事前準備的子彈,正在思考應該怎麼處理這顆子彈的時候,碰巧有一個非裔美國人婦女在推送要換洗之床單的洗衣籃,鄭急中生智,就把這顆子彈丟進該洗衣籃中,以免被警方查到相關證物。
當天下午檢方就開庭審理該案,黃和鄭兩人均被裁定拘留。

刺蔣案的法律鬥爭
在刺蔣案演變成黃鄭兩人的法律案件之後,鄭先於1970年5月26日以九萬美金被保釋出來,而黃文雄則是在7月8日以十一萬美金被保釋出來。在整個訴訟過程當中,黃鄭兩人決定採用的基本策略是「黃認罪,但鄭不認罪」。鄭不認罪的話,舉證責任就變成是檢方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提供鄭槍枝的陳榮成,就變成是該事件的關鍵性證人。鄭這樣描述這個法律鬥爭的梗概:
「彼當陣ê策略啦,就legal battle[法律戰爭] ê策略啦,就是講,黃文雄承認伊有罪,伊就證據攏tī檢察官彼pêng嘛,伊是講伊有罪,ah我無承認我有罪,ah你就愛證明我有罪啊。」
「Ah beh證明我有罪,ah唯一個證人就是陳榮成嘛。Ah我彼陣就chhōe蔡同榮,講,ah你主席你愛緊[快]處理這個代誌啊,你愛緊khà電話h³陳榮成啊,叫伊趕緊離開Louisiana[路易斯安那],請假iah是啥hⁿh,ah伊檢察官這pêng ê調單[調查單] hⁿh,調過去hia chhōe無人,無代誌,就m̄免[不用]出庭啊。」
「Ah蔡同榮,m̄知是啥物原因啦,m̄願意khà[打]這通電話,hⁿh,ah尾仔[後來]脫kah,伊khà[打]去ê時陣,陳榮成講,bē使[不行],這警察已經tī in[他]兜[家]啊。Ah警察就kā陳榮成押來New York作證。出庭作證ê時,我就歹[很難]講無[沒] involve[參與]啊。」
「所以到尾仔法庭是判我有罪,jury[陪審團]判我有罪。所以阮二個就是講,一個被判有罪,一個承認有罪,ah法官就講,ah lín[你們]二個攏有罪啊,hⁿh,ah伊定一個日期啦,這日期我chit-má bē記啊,彼日lín[你們]愛出庭,伊beh宣判。」
在被陪審團判決有罪的當天,黃鄭兩人就找律師商量此事,並做出棄保逃亡的決定。鄭這樣說明做這個決定的經過:
「Ah彼日,阮就去chhōe律師啊,阮決定講,這無需要去h³關啊,阮ê意思就是講,走離開美國,h³這個獨立運動ê聲hⁿh,chhōa[帶]離開美國,ah你走到toh位[那裡],這個聲會tòe[跟]你走啊。所以阮就kā律師講,阮可能bē出庭啊,會走離開美國啦。Ah我ê律師講,this is your decision[這是你們的決定],這lín [你們] ê決定啊,lín[你們] beh an-chóaⁿ做攏會使[可以]啊。hⁿh,án-ne,beh開庭ê時,阮就已經離開啊。」
因此,在1971年7月6日的正式刑期宣判庭之前,鄭就已經拿著其他台灣同鄉的護照飛到瑞士去了。透過曾經擔任過「瑞士台灣同鄉會」會長之同鄉黃瑞娟的幫忙,鄭找了一位瑞士律師,諮詢其尋求瑞士政府之政治庇護的可能性。不過,經過這位律師的分析之後,他覺得拿到瑞士之政治庇護的機會並不大,所以又轉往瑞典。他是這樣講的:
「一個[台獨聯盟]盟員,一本護照借我,因為我tī美國無護照啊,國民黨ê護照也無,美國護照mā無,所以借別人ê護照,我就àn美國飛到瑞士啊。」
「到瑞士彼pêng,因為世界各國攏有同鄉會嘛,去到瑞士彼pêng,是一個,khah早bat[曾經]做過in[他們] hia[那邊] ê會長--ê,叫黃瑞娟,黃瑞娟我就去tòa tī伊hia,伊mā足[很]熱心--ê,就tī瑞士,chhōa我去chhōe律師啦。看會凍[可不可以]請政治庇護bē。」
「就去chhōe律師事務所hⁿh,ah伊內底[裡面]有一個少年ê律師,我想講,喔,伊這外國人實在真好hⁿh,伊同情這個代誌hⁿh,擱請我去in[他們]兜[家]食飯,喔,in[他們]這食飯hⁿh,攏擱點蠟條[蠟燭] ê neh,ah食飯擱食了bē-bái[不錯] neh,ah伊chiah[才] leh分析這個代誌。」
「伊是講,這款代誌hⁿh,beh tī瑞士請政治庇護hⁿh,這機會足[很]低(kē)--ê啦。伊講這瑞士kap美國ê關係hⁿh,這瑞士無啥可能會准這個代誌。Ah伊kā我分析講,唯一可能ê國家,是瑞典啦。」
就這樣,鄭從瑞士又飛到了瑞典。他先是住在斯德哥爾摩的YMCA,然後又透過洪鎌德聯絡到彭明敏,再輾轉和瑞典教授Bernard先生 --- 這位彭明敏在從台灣逃亡到瑞典時、提供其幫助的「國際特赦組織」成員 --- 接上頭,最後由這位教授幫忙鄭申請瑞典的政治庇護。
鄭雖然順利取得瑞典的居留權,然而在美國的要求下,他又在1972年六月面臨被引度回美國接受判決的命運。於是鄭決定絕食抗議,同時瑞典的輿論也迫使瑞典總理不得不做出二項承諾:第一,要求美國不得將鄭交給國民黨;第二,當鄭在美國服完刑期之後,歡迎其回瑞典定居。在整個的引渡過程中,鄭先後在瑞典、英國及美國的監獄待過,直至1974年年底服完刑期,返回瑞典定居。
鄭在返回瑞典定居八年多以後,隨後又移居加拿大八年,最後於1991年六月「翻牆」返回台灣。
返台
1991年一月,由於鄭的岳父過世,同樣被列為國民黨黑名單的鄭現任妻子吳清桂終於拿到台灣的簽證返台奔喪,讓鄭這個飄流異鄉的台灣遊子燃起了返鄉的希望。同年六月,鄭終於用自己的方式「翻牆」回台,但卻在公開現身後立刻遭警方約談,並在同年十月因「擅自入境」違反國家安全法,被台北地院判刑一年。1992年七月,台灣高等法院駁回鄭的上訴,維持一審一年有期徒刑的判決,並不得緩刑。同年十一月,鄭被捕入獄,直到1993年十一月才刑滿出獄。
在鄭入獄前,他就已經和其成大時的同學王俊雄連繫,決定參加「二二八紀念碑」的公開競圖比賽。正當紀念碑設計到一半的時候,鄭卻因非法入境案被捕入獄,使得整個設計工作頓時受到重大的挫折。為此,王俊雄等人就利用每次到監獄探視鄭的機會,扛著設計模型,在監獄的會客室中隔著玻璃和鄭討論設計草圖。結果,這個作品竟然獲得該競圖比賽的首獎,成為1995年設立於「台北新公園」 (今「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之「二二八紀念碑」的興建藍圖。這個紀念碑係以圓椎與立方體複合的構成,而評審對這件作品的評語則是「達到抽象的、追悼性的精神境界」。鄭在建築設計上的專業能力,在這個作品中表露無疑。
除了這個比較出名的「二二八紀念碑」以外,在南投縣草屯往埔里的中潭公路上,一座高達12.5公尺的陶製地標,也是鄭的作品。東海岸的風景線上,鄭的作品更是星羅棋布:從花蓮鯉魚潭的觀景樓台、大興瀑布紀念公園的彩虹鋼構、富里鄉六十石山的尖閣寺,到台東縣鹿野高台、關山等地的休憩亭閣,都是出自他的手筆。
此外,鄭還在幾年前迷上長跑,單是2004年一年,他就參加了六次半程的馬拉松比賽(廿一公里)。
鄭目前定居台北,在建築師事務所工作,同時也在業餘從事油畫創作。